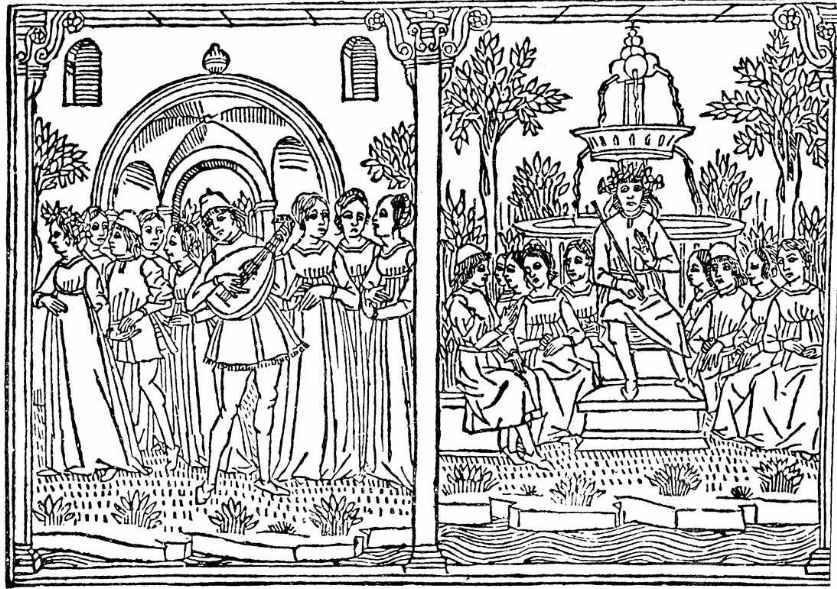那一天,和伯父通完電話,我半玩笑的說:「老爺子,來杭州消遣消遣,找找當年的感覺」。
我不報希望他能來。相識十幾年來,都是我路過他的城市,做客一般,到了停,去了走,連吃帶拿,從沒失過手。
父母過世後,那個城市,那個家,成了我的精神領地。他自然而然的接過了父親的角色,噓寒問暖,寫信夾帶些零錢 ,不厭其煩的鼓勵我學業。外人看來,這是我的幸運。記憶里,仿若都是他帶著怯生生的我,買車票,買各種必需品,要麼,逼著我吃東西。
他信里說:「我看你,就像看剛學走路的孩子,只要不倒,就讓他一直走下去,要倒時,一定要扶的」。我沒走上歪路,讀完書,在杭州扎下根,這話,大約起了很大作用吧。至於一起找閒遊玩,實在不曾有過。他居然爽快答應了。這讓我很興奮,無論如何,血脈相連的親人來看你,總是快活的事。
接站的細節很快有眉目了。杭城的5月,草長鶯飛。但已經熱過了頭。人群中看到他,居然有些恍惚。倆人站一起,倒顯得我胖壯些,他的淺黃夾灰格外套,我很熟悉,笑意盈盈,我也很熟悉。我搶他的背包,他不讓,風風火火的前面走。這是老人的習慣,我就隨他意。過馬路時,他不再堅持,我們挨著走,我能看到他眼角的細紋。伯父老了。依然聰明和要強,但開始妥協。我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,發質濃密,清癯儒雅,心氣極高。隨著歲月流逝,卻溫和起來,讓人感嘆衰老的霸道和不期而至。
和家人報過平安,諸事定了個大概,我們開始計劃出行路線。伯父的意思,西湖看過多次了,不喜人造景,最好麼,有那種人跡罕至的山溝之類。但有幾個古鎮,南潯西塘要去的。他在家做了功課。還拿出兩個黃皮的筆記本,裡面記載了周易風水之類的東西(他認為江浙的風水好)。我心裡暗笑他的迂,都啥年代了,玩就是玩,還要找龍頭找寶藏啊。伯父很開心,因著我的旗號,可以獨自出來,這機會並不多,骨子裡,他還想證明自己,身體很OK。他輓高了褲腿,窩在沙發里,翻著自己的路線圖。從鼻梁的眼鏡里,抬起眼,盯著我說:「我這次來,也是要看看你,到底怎樣了,終身大事該解決了。不能總拖著,我不管誰管你呢」。
這並不是我的負擔,我已經有了心儀的目標。但姑娘還在遲疑。這種事,剃頭挑子一頭熱是不行的。就在接站前,我還幫姑娘買了回老家的車票。伯父熱情很高,前後問明大概,巧的是,姑娘的叔叔,居然,就是他的老朋友。只是多年未見。
那一夜,伯父幫我分析和姑娘交往的細節,依著自己的經驗,高談闊論,簡直比自己戀愛還上心。這讓我覺得,老小孩很好玩。爺倆之間,除了瀰漫著親情外,還像極了哥們,朋友,默契和諧,和親生父親,是斷然不會這樣。
那一晚,我們都睡的不好,我,是因為這兩代交融的興奮,他,大概是坐車累到吧。 次日先去了烏鎮。老實說,烏鎮並不好玩,言過其實,人聲噪雜,船有什麼好坐的。我爺爺,解放前,自己有船,從老家白河河道,經漢江,到武漢,來來回回。伯父也覺得無聊,古鎮不是他想象的樣子。在臨街的一個小店裡,伯父買了一張烏鎮的地圖,這就算來過了。至今我懷疑,他的不坐船遊玩,是怕我花錢。他在銀行多年,兒女事業有成,龍鳳呈祥。卻並無大手大腳的習慣。我不知道,這是否是一個糟糕的出行經驗,對我而言,和他去哪裡,都無所謂。對他而言,江南水鄉是這樣,還不如未看到更好。
轉回杭州,我私自決定,哪裡也別去了,難不成還跑到臨安的山溝裡去?老爺子萬一有個磕磕絆絆,我罪過大了去了。我哄著他,說黃龍洞過棲霞嶺,到岳王廟,這一段竹林小徑清淨,嶺上面還可以看湖景,安逸就好,不拘去哪裡。他應下了。是夜無話。
我很享受這個時刻,多年以來,我不記得有父輩的人,和我如此親近,快意青山,莫逆於心。不講話心裡也美的很。
棲霞嶺上,我記得一個細節,老爺子犯煙癮了,我故意逗他,說有查崗的,他信以為真。自己搖頭苦笑,說戒不了了。我正告他:「戒不了算了,林副統帥,不煙不酒,活了63,周副主席,只酒不煙,壽止73.,毛委員呢,只煙不酒,是83,我們的小平同志,既煙且酒,高壽93.。少帥學良,吃喝嫖賭,五毒俱全,活了103歲,只有我們的雷鋒同志,五好青年,無任何不良嗜好,可惜才23歲就犧牲了」。伯父哈哈大笑。
棲霞嶺他覺得走的不過癮,我們走了兩遍,一點都不累。那天,我們在河坊街的一家本地杭幫菜館裡,我點了西湖醋魚,宋嫂魚羹之類和青菜,還要了啤酒,手剝筍很對伯父的胃口,伯父喜煙不酒,破天荒喝了兩杯。在城隍閣的圍牆邊,我執意要和伯父合影,他不肯,說不上相,太難看。很奇怪,至今我沒有和他的合影。後來,我們之間彷彿約定過,再沒提起過這三天的所謂遊玩。
臨晚,他說沒啥玩的了,想回老家一趟,很堅決,並且要去看那姑娘的叔叔,他的老朋友。我知道,他想要上門提親了,來個速戰速決。那我還怕啥子麼。這是我一見鍾情的姑娘,剛強麻利,眾星捧月,能娶到她是我一生的福氣。回去的車上,伯父少講話,沈浸在他的風水周易上。時而回頭看看我。我不知他如何作想。車過太湖,水波浩瀚,我們一同望向窗外,我有些難過,這樣的場景,怕以後沒有了。
坐長途車是一件痛苦的事,我帶著一本書,是美國女作家卡森•麥卡勒斯的《心是孤獨的獵手》,我還記得那開頭:「鎮上有兩個啞巴,他們總是在一起… 這開頭讓人很著迷。麥卡勒斯是張愛玲式的天才作家。我很喜歡。
老家所在市是一個文化古城,古戲文里經常會出現。到站還是凌晨4點多鐘,在表妹那裡暫時安歇,爺倆一起煮方便面,湯湯水水,喝個一乾二淨。人餓了,吃啥都香。伯父神秘的對我說,出去走走,我沒料到,這個地方,居然是他十幾歲生活過的。這個早晨有點早,有點涼,看不見任何行人。
他站在陌生又熟悉的路口,講起當年父離子散,寄人籬下的情形。風漫過街道,我看見他眼裡的憂傷。這些故事我是聽過的,這次尤顯的真切。我突然覺得很幸運,即便是他自己的孩子,也從未有這樣的時光,如果我能夠,我願意,永遠保存這些複雜的情緒。
那次提親,其實很失敗。這個後來成為我媳婦的姑娘,一口就回絕了伯父的提議。我們事先商量好,如何上門,如何開口,如何婉轉逢迎,在意氣風發的我媳婦面前,都不堪一擊。後來伯父告訴我,他很難過,一是沒完成任務,二是被小姑娘堵的無話可說,有些傷自尊。他說,活了那麼大歲數,沒忙過這樣的事。沒經驗。不過我們爭取了,謀事在人,成事在天,天涯何處無芳草。那姑娘有些厲害,怕你倆成了,還受欺負呢。
那天,旅途勞累,我們一起去了大澡堂子,舒服的泡了下,這是我第一次和伯父坦誠相見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他很瘦,但骨架勻稱,背有些彎曲,是早年成分不好,虧了力。第二天,伯父就回了他自己的城市。瞞著我們所有人。我其實有第六感,趕到車站,車沒走,我看著他背影,卻並無怎樣的留戀。他有他的老年生活,要帶孫子,要應付腰疼腿疼,當然也沒什麼我好擔心的。老夫老妻,當年風雨雷電,到了年紀,客氣起來,還拌著嘴,那埋怨里也透著些矯情。人老了圖個什麼,不就是家和萬事興。他家換了大房子,添了小外孫。林林總總,都是高興事。
在我單位的馬路對面,有一片新建的教堂,那圍牆上寫著:
“在至高之處,榮耀歸於神,在地上的平安,歸於他喜悅的人”
每天班車飛馳而過,我都能讀到它。
又一日,讀清代詞人黃仲則的《感舊》—
從此音塵各悄然,春山如黛草如煙。
淚添吳苑三更雨,恨惹郵亭一夜眠。
詎有青馬緘別句,聊將錦瑟記流年。
他時脫便微之過,百轉千回只自憐。
- 文章轉自網上,犯刪。